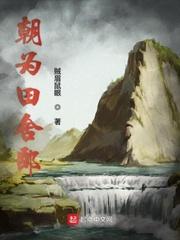笔下文学>娘娘她宠冠后宫 > 第332章(第1页)
第332章(第1页)
她只字不提证词里的那些内容,诉说着自己的委屈:“妾身没想到一时放任,竟出了这样的事。”
唐文茵的声音几不可闻:“殿下是说自己一无所知吗?”
“蒹葭的证词,殿下可瞧见了?蒹葭是云选侍贴身宫女,云选侍疯了后,常对她动手,妾身于心不忍,便将她调到了尚食局。自然,妾身这样做也是有私心,毕竟一夜之间,沈庶人殁了,云选侍疯了,这样大的事却查不出结果,实在闹得人心慌慌。”唐文茵忽地变了脸色,“因着妾身对蒹葭施以援手,蒹葭便将所有的事情托盘而出,并按下了手印。”
郑初韫目光一转,“唐妃早就知晓了真相,为何不告知于本宫或是陛下?”
“妾身想放长线钓大鱼,看看幕后之人知道妾身将蒹葭保护起来之后会不会着急,会不会动手。可妾身等来等去,也没发现异样,正以为蒹葭是胡编乱造时,殿下您说巧不巧——”
郑初韫神色微妙,只见唐文茵眼底闪烁着厉色,冷笑道:“就在妾身来乾坤殿前,蒹葭死了。”
“敢问殿下,对蒹葭一事毫不知情吗?当晚,云选侍是收到了您的消息才去的静安宫,可云选侍去时,沈庶人已经没了气息。云选侍因此被吓疯了,还被诬蔑成杀害沈庶人的凶手。”
郑初韫气定神闲地看着她,“仅凭蒹葭的一人之言,唐妃便认定了是本宫所为?本宫与沈庶人无冤无仇,何以到要了她性命的地步,更何况,本宫何必加害于云选侍?”
“本宫管理后宫,行事向来公允,也一向告诫嫔妃和睦相处。本宫是皇后,处事公正,从不偏颇怠慢任何人,自认问心无愧,唐妃,你从前行事冲动,不计较后果,本宫也多次教导你,给你锻炼的机会,怎么过去这么久,你还是不曾长进?”
她一字一句,说到最后,还叹息一声:“唐妃,云选侍与昭妃是故交,蒹葭又是云选侍的婢女,你与昭妃也算亲近,焉知蒹葭的话有几分真,几分假?先不论云选侍为何会从静安宫出来,当时御花园那么多人,云选侍为何冲撞昭妃?想必昭妃还记得,云选侍疯了之后,嘴里还念道着&039;沈姐姐&039;呢。”
“唐妃,并非是本宫怀疑昭妃,只是这些证据实在太过单薄了。”
唐文茵眼眸一低,她早知郑初韫不会被这些证词镇住,但没想到她说着说着,竟将矛头指向了沈听宜,还暗暗挑唆起她与沈听宜的关系。
只能说,不愧是世家的贵女,素来行事滴水不漏的皇后啊。
可惜,她这一次做足了准备。
唐文茵从袖子里取出一张纸,笑吟吟地给她看:“这是今儿莲淑仪特意来承乾宫写给妾身的,殿下不妨瞧一瞧。”
郑初韫神态平和地接过那张轻薄的纸张。
唐文茵静静地瞧着她,语气轻缓:“从静安宫出来,有两条路能到御花园和后宫各处,其中一道便要经过玉照宫,莲淑仪住在玉照宫,可是瞧见了不少事呢。”
郑初韫眉心压低,抿着唇没说话。
唐文茵自顾自说着:“当初姜御女如何从静安宫出逃,如何自缢在了长乐宫;云选侍又是何时到了静安宫,如何从静安宫出逃,到了御花园,旁人不清楚,可玉照宫的人看得一清二楚。”
她好整以暇地道:“殿下不会要说,莲淑仪说这些,是为了昭妃吧?”
沈听宜与莲淑仪不睦,宫里人谁不曾耳闻。
郑初韫掀眼,面容沉静,语气平淡:“即便如此,莲淑仪所说的这些,又有什么证据呢?”
“唐妃,本宫知道你与昭妃交好,你心里急于找出害昭妃的凶手,可本宫,有什么理由害昭妃?”
唐文茵轻扯了扯唇:“殿下,难不成妾身能买通所有玉照宫的人,逼迫他们指认吗?不论旁的,敢问殿下,妾身又有什么理由攀咬您呢?妾身是奉陛下之命调查,有了这些证据,可殿下却觉得口供都是假的。殿下不信妾身,难不成要觉得妾身会故意陷害您吗?”
郑初韫眉心一跳,唐文茵却不给她再次开口的机会:“殿下应当还记得闲云吧?”
闲云?乍一听到这个名字,郑初韫还没反应过来。
唐文茵徐徐道:“当初闲云死在了衍庆宫,虽说也没有明显的证据,可所有人都以为是贞妃。贞妃当时有孕,无暇顾及此事。后来被查出的冬也,是沈庶人的耳目,这一点证据确凿。闲云是淑妃的婢女,淑妃生前与沈庶人是手帕之交,因而淑妃病逝后,闲云同沈庶人来往亲密,此事后宫皆知。”
她说了很长的一段往事,话锋忽然一转:“闲云的死,同时打击了贞妃和沈庶人,贞妃被人怀疑,因此禁足,而沈庶人则失了亲信。”此事,两位宠妃的矛盾也被激发扩大,谁获利最大?唐文茵没有明说,但任谁都能听出她的意思。
“沈庶人被废后,长乐宫的一众宫人都进了宫正司受审,长乐宫的掌事太监周长进吐露出一些事情,他说闲云在失踪前,曾给沈庶人写了一张字条,可惜他不识字,那字条也被沈庶人烧了,只是沈庶人因此发怒,叫人看住了司药司,然而等了一夜,都没有等到闲云,甚至整个尚食局也没有找到闲云的身影。这之后,闲云的尸首就在衍庆宫被人发现了。”
唐文茵不紧不慢地说着:“闲云死后,她的屋子被翻了个底朝天,却是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找到。妾身最后一次见到闲云,是在御花园,她见到妾身时急匆匆的模样,妾身问她怎么了,她说淑妃的忌日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