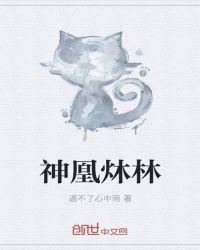笔下文学>最美好的年华遇见最美的你 > 做生意赚钱并不容易(第1页)
做生意赚钱并不容易(第1页)
从县里转车回到家,远远地,甄亦凡就看见在晒塔里翻晒麦子的妈妈。走近了,抬起头想喊一声“妈”,却先映入眼帘的是母亲鬃边又增添的一缕白发,他一时喉咙哽咽,竟然未能喊出声来。
进了屋,放下行李。妈妈问他在车站下车时看到老四没?这些天,老四天天到车站等他。上个月下大雨时,他们几弟兄在河里捞了一些鱼,本来足够一家人饱餐一顿的,却为了等他这个当大哥的,老四不准吃。把鱼放养在水缸里,隔两天死一条又捞出去,半个多月来,现在水缸里的剩下几条鱼只够打汤喝了。老四的兄弟情意,让甄亦凡很是感动,他放下行李回转街头,去寻找等他回家的老四。
这个暑假,甄亦凡没打算在外面搬砖赚辛苦钱,他想跟着父母学做生意。再有一年就要毕业了,祖祖辈辈都是农村人,都在这个田无半亩的大山里。对于一年后分配工作的事,他心里没有一点底。倒不如乘着暑假两个月跟父母学做生意,到时万一工作没分配好也有一个挣钱讨生活的门路。再说,四年级开销也比以前大了,除了一直没告诉家里的学费上涨外,物价通货膨胀带来的生活费上涨,加上实习阶段经常往外面跑开支肯定大一些。这些,他也不好意思向父母伸手。这几年,除了他读中专,老二也上了中专,老三读高中,老四读初中,到处都要钱。他只好学着“自力更生”,哪怕减少父母一点点负担也是好事。
对于大儿子的想法,父母也没有反对,村上跟他差不多大的人早早开始干农活或者南下广东浙江一带打工赚钱。甄亦凡虽然初中起放假就帮着在街市上卖粮食,但在永顺这边收粮食还没有试过。乡里的小本生意也无非就是从湘西那边低价收购大米、苞谷、黄豆、绿豆等一些粮食,然后回到桑植本地集市上又卖出去,中间赚几分钱的差价。还有就是两地的计量不一样,永顺属湘西民族地区,量米的“升子”,桑植这边的是标准的两斤,而永顺那边不太标准是两斤四两,甚至有两斤半的,大小就要看自己的眼睛了。还有平升、尖升的量法,平升就是将米装满,上面抹平,而尖升就是尽管让你堆,不管堆多高只要不滚下来都是你的。除了计量之外,还要分清品种,好米和差米价格自然不一样。最好的砂坝“颗砂”米,据说以前是皇宫贡米,只有砂坝方圆几十上百亩好田出产,煮饭软糯、清香可口,是这一带最好的大米。只要收到了,每斤差不多可以赚个角把钱。县城里每次都有人到利福塔这边高价收购,转手卖给城里干部。还有就是碾米,是用水碾坊碾出来的米,颗粒完整,卖相好。最差的也就是最常见的机械打米机打的米,细碎不好看。
当然,还有“玩秤”一些小手段,就是买卖过称时玩一些小动作,赚点“昧心钱”,这些就不是甄亦凡能够学得的了。所谓玩手段的都是做短期生意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至于“卖”这个环节,最要讲公平,而且要尽量货美价廉,只有这样才一能培育长远的顾客,短斤少两赚“昧心钱”的做法是自断前途。没有人上了一次当还会上二次。甄亦凡父母也从来没有玩这些小手段,做生意几十年靠的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要不是也没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也赚不到钱送他们四弟兄读书。
甄亦凡想自己独立去做生意试试。刚好父母那段时间和别人合伙到乡下收购油菜籽往县城粮站贩卖,也就同意让他独立试试这块生意,把他交给了一个本家爷爷带,70岁了,一起做生意的人都叫他“甄伯”。
第一次做的生意是去县城粮站拖苞谷,然后到乡里集市分散卖,就赚中间的3到5分钱价格差。赚这个钱一是信息差,老百姓基本上不知道县城粮站有苞谷卖;二是粮站不零售,成吨卖,一般老百姓喂猪买不了那么多,而且买几十斤去县里来回花车费也不划算,倒比集市里带几十斤还贵一些。
一大早甄亦凡就动身去沙湾里邀甄伯,其他生意人这段时间都忙着收购油菜籽,价差大一些利润也就高一些。集市的苞谷生意就留给了这一老一少,一场起码能够卖出去两三吨。赶到甄伯家里,他家人告诉甄亦凡甄伯山上忙农活去了,下午两点再去县城拖苞谷。
下午两点甄亦凡再去,这次甄伯在家里等他,两人又上街找到司机“黄狗”,请他的拖拉机拖苞谷。几人开着拖拉机“突突突”直奔县城。到了县城甄伯轻车熟路找到粮站主任开单子、交钱,到粮库拉货。两个人,一老一少,从粮仓里抬出200斤一包的苞谷装上车,也累的够呛。第一次试,甄亦凡只要了一吨,2000斤,每斤赚5分钱差价,刨去20元运费,只要不折秤,一天卖完也能赚80元,相当于他学校一个月的生活费。要是一天卖完了,第二次就多进点货。回到家里在市场上卸好货快晚上8点钟了,父母和三个兄弟都还等着他开饭。虽然还没开始卖,他也感觉到了做生意的不容易。
晚上听父母讲,他们与人合伙收购的油菜籽今天在粮站没送出去,主要是水份超标。现在一些老百姓也变狡猾了,为赚生意人几个钱,有人将没晒干的油菜籽掺在麻袋的最下面,他们也没办法一插到底,导致一车菜籽不过关,要第二天在粮站再晒一天。也不知道再晒一天又会亏多少斤两,到时是赚钱还是亏钱还说不定。其实油菜籽没干还好,更有那没有良心的,在最下面的菜籽里掺沙子,不过也不敢掺多,一多斤两就不对了,常年干粮食生意的人也不是马虎角色。遇到这样的人,做生意的是倒了血霉,耽搁工不算还要赔钱。
第二天还好,甄亦凡和甄伯拖的2吨苞谷都早早卖完了,主要是大部分生意人这几天都去做油菜籽生意,没人和他们争顾客。到下午收工算账,刨去成本和车费再加上折秤,赚了76元钱,也算“旗开得胜”。甄亦凡自然是特别高兴,拿出2块钱在屠夫那里割了一斤肉,回家做好了饭菜,等着去县城送油菜籽的父母回家一起品尝初次出战的胜利。
晚上,甄亦凡提出明天跟大家去砂坝收购大米回来卖,父母也没反对,给了他1000块本钱。
第二天一早5点多钟,甄亦凡和父母就起床了,天还是麻麻亮。他们一起出门,父母他们一行人下乡收油菜籽,他和甄伯还有几个人去砂坝收购大米。
坐在拖拉机的车斗里,一路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才到砂坝集市,大家各自散开收购大米。这些年来,收购的生意人和这些卖米的老百姓都成了老主顾关系,老生意人根本不需要四处去找卖米的人,只要坐下来在那个经常收购的摊位上,卖米的人自会找来。甄亦凡是个生面孔,没有人愿意把米卖给他,也没有其他生意人给甄亦凡父母的老主顾介绍他,一些人巴不得甄亦凡父母没来多收一些呢,收得多自然这一趟就赚得多。他也不能自己提高收购价格,一来本来差价就那么几分钱;二来大家约定好了的不能乱涨价或降价,不论买还是卖,要是随意扰乱市场行情,这小本生意大家也都没法做下去了。
甄亦凡差不多是逢人就问“有米卖没?”可见到他是个生面孔,没有人把米卖给他,要么就抬价想从他身上赚几个辛苦钱,要么同等价格干脆卖给老面孔。有人担心没卖给老主顾以后卖不出去,有时米差了都不愿收购,这时老主顾也会看到面子上便宜一两分钱收购,免了背回去的苦处。也有人担心甄亦凡这个生面孔玩手段,这边的老百姓都很朴实,宁愿吃亏在明处也不愿上新人的当。
从早上到中午,甄亦凡一颗米都没收到。中午,大家伙汇聚到一家面馆充饥。甄亦凡早上出门只吃了一碗面,此时又累又饿,可他只在面馆里喝了几杯水解渴,他没舍得两块钱的面钱。没收到米就赚不到一分钱,来回的3块钱车费还是要出的,要是收到米100斤另外还要1块钱的车费。今天不但没赚到钱,还亏了3块钱车费,2块钱的面钱,他自然也就不敢再亏了,只好饿着肚子。整个中午,别人休息、喝酒,而他只是呆呆地坐在角落里,听着电视机里《新白娘子传奇》一遍又一遍唱着“千年等一回,等一回啊,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啊,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只为这一句啊哈断肠也无怨……”。“不吃碗面啊”甄伯上前安慰他,“我不饿”,甄亦凡有些感激这位老爷爷,“不要紧,下午还没收到米我明天带你去县里拖苞谷”,“谢谢甄伯”“傻孩子,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呢”,甄伯有些心痛这个懂事的孩子。
一直快到天黑才返程。后面甄亦凡好歹收到300斤大米,也算没打空手。不过看到别人都是满载而归,早上带的麻袋都是满满当当的,一个二个在车上算这趟又赚了多少钱,甄亦凡总有一种挫败感。坐在堆成小山一样的米“包子”子上,甄亦凡也顾不得其他,两只手紧紧抓着米袋子,生怕一不小心被颠簸下去。看着对面七十岁甄伯花白的头发和胡子,想到父母不管六月的炎热还是寒冬腊月的寒冷都是这么辛苦过来的,这一刻这个学生也理解了生活的不容易。
天完全黑了下来,夏天的蚊子一群又一群,咬在脸上、腿上、胳膊上,又热又痒。他们熟练地把空麻袋套在大腿上,甄亦凡也学着大家在双腿上套上空麻袋,厚厚的麻袋蚊子叮不透,虽然又闷又热,不过总好过被蚊虫叮咬。
回家后,甄亦凡把一天的过程给父母说了,母亲没有责怪他,而是告诉他,下次她亲自带他去。“我和那些老主顾讲一讲,让大家都认识你!那边的人都是讲感情的,有时宁愿吃点亏也只认老主顾”。
第二天,甄亦凡又和甄伯去县城拉苞谷,因为上次卖得挺顺利的,这次就多拉了1吨,每人3000斤。不料第三天逢场时却没有卖完,都剩下1000多斤,看来下一趟不用去县里进货了。
集市过后第二天就是永顺砂坝的场,要过去买米进货。这一次,甄亦凡母亲停下收油菜籽的生意带他去认识那些常年来打交道的主顾。一下车,就有不少人背着米、挑着担子围上来“梅花姐,上一场怎么没看到你来收米呢?”有人把自己肩上、背上的大米放下来问他母亲,“我这几天忙着下乡收油菜籽,你们这边不种油菜我就没来。这个是我家老大,今后大家把米送给他,不会亏待大家的。”“哦,是你家大相公啊,前几年不是考上省里中专么,还出来做生意?”一个挑担子的中年大叔问。“放暑假在家里没事,大人又忙不过来,我想试试做生意”,甄亦凡主动接过话。那边母亲在过称收购一个婆婆的大米。“是个懂事的孩子,大姐,你可有福气了”,挑担子的大叔也把自己的大米送到秤前。
“32斤,9毛钱1斤一共28块8毛”,甄亦凡从小跟在做生意的父母身边,心算极快。等母亲过完秤他就随口报出了结果,数出票子递给老婆婆。“梅花啊,你帮我再算一算”,老人有点不放心,生怕小娃子算错账,要甄亦凡母亲再算一遍。“婆婆,我儿子没算错,你放心”,“那我就放心了”,老婆婆接过甄亦凡递过来的钱转身走了。“来来,先称我的”,一位妇女把背篓里的大米递给甄亦凡,“30斤,27块”,甄亦凡很快就报出斤两和价格,其实还有半斤秤没报出来,除去蛇皮袋预定的2两皮重,还有3两米。卖米农妇先前在家里也自己过了称,总会留出几两到半斤的“寸头”给收米的生意人,要是一点都没赚头,也没人做这个生意了,因此收购时少几两秤也是公认的。要是几斤不对头那就“黑良心”了,几次下来就会坏了自己的名声,再也没人把米卖给你。“不愧是大学生,算账这么快”,农妇一边接过钱一边夸奖他。乡下把考进省里学校的一律当大学生,也分不清大中专本科什么的,反正就是毕业国家分配工作吃上了公家饭。有一些赶场卖米的农人其实不识称也不会算账,上过当,因此只相信老主顾。“以后就由我家老大来这里收购了,大家放心,万一搞错了账也可以找我的”,甄亦凡母亲一边手上不停称秤,一边向老主顾介绍自己的儿子。
甄亦凡曾听到一起跟父母亲做生意的人讲过一件事。有一次母亲收米时忙中出错,把一个人的钱少给了一块,中午休息对账时才发现,她硬是停下下午的生意,找了几个人打听到卖米人的住址,又走了几里山路把钱送到事主家里才心安。也因为那一次,那一方的农户卖米多年来都只卖给她。这话甄亦凡算是相信了,那天第一次出来做生意一个上午没收到一粒,下午甄伯只对几个卖米的说了句“这个小伙子是梅花姐屋里的老大”,就有几个人围上来把米卖给了他,也让他不至于第一次做生意空手而返。这一天的收获不错,总共收了1500多斤,还有几十斤“颗砂”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