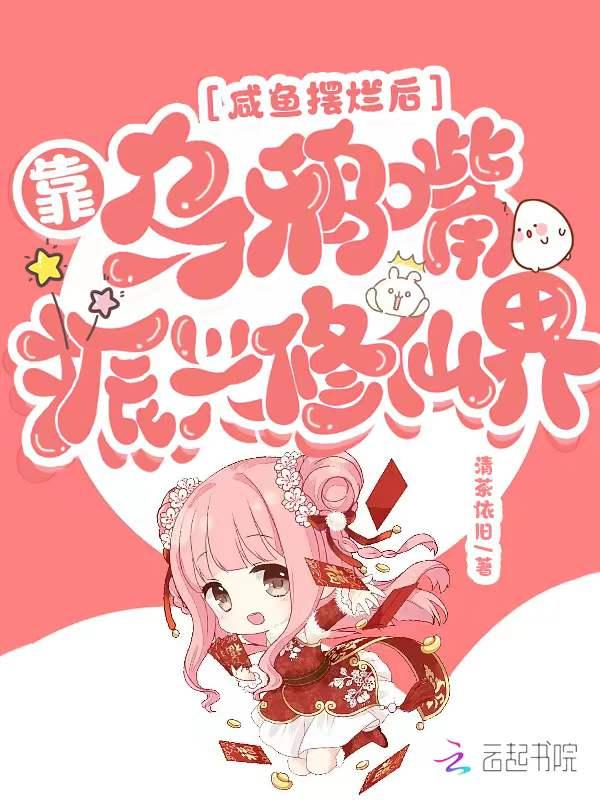笔下文学>越流清歌的 > 二十春日迟(第3页)
二十春日迟(第3页)
吴行歌见钱传瓘进入车厢中已有一盏茶的时间,从她所立之处听不到任何动静,而来人的车夫个个虽状若随意地整理马匹,却始终将她二人罩在眼风之下。不由得忧心渐起,忍不住向车厢走去。
突闻得“哈哈”的畅笑声,钱传瓘掀开帷幔步下车厢。
钱传瓘走到越葳身前道:“越葳,我与梅弗问是相识多年的好友,很可信赖。他可护送你回西府。”
越葳垂目低眉,沉静不语,似在思考什么。
吴行歌想起莫留阁中那月白长衫清冷的身影,不由问道:“明宝哥哥,将带着伤的越葳孤身一人托付与他,你很信得过他?”
钱传瓘望向帷幔低垂的车厢,目中有着如春日草芽破土而出般的欣然的光,说道:“我们,是过命的交情!”
令越葳犹豫的,并非是否回西府——先前她坚持的是不能令钱传瓘为了送自己回西府而耽搁了时间。而现在毋须钱传瓘将她送回,他可即刻赶赴常州。她也愿意信任钱传瓘对梅弗问的判断。
令她思考的,却是另一件事……
她抬起头,对吴行歌递出一个勿虑的微笑,走向马车。
慢且稳的步子落在道上,行过为首的车夫,经过第一辆车驾。
套着第二辆舆厢的黑马呼呼地喷着气,墨色帷幔近在眼前,似乎能闻到绿萼白梅散发的幽香。
白梅忽地飞去,日光洒进舆箱中,明暗交错间慵懒地倚着的那人嘴角噙着一抹淡笑,“越太医,今日一早鹊啼枝头,原来是告知梅某我这么快便可再见国医圣手之面。”
目送马车离去,钱传瓘与吴行歌各自上了马,调转方向往常州而去。
“明宝哥哥,我听闻那梅弗问平日居于西府。他为何会经过这荒野之地?”
钱传瓘道:“他的身世颇为可怜。其父为家族中坚人物,原定的承继祖业之人,其母非正室。他出生那日其父正在外经商,突发急病而死,竟与他的生辰同一时辰。他出生即失父,又被视作克父的灾星,为家族所不容,更为父亲正室所恨恶,而祖业落于二叔之手。正室将他们母子俩逐出梅家。其母绝望之下带着他投河自尽,被灵岩山寺的僧人所救。之后在其小叔的接济下艰苦偷生。其母祈愿弗问得以重回梅氏,认祖归宗。后梅家几支的男孙均早逝,终在六岁时被族中长辈接回祖宅。其母自此每隔三个月便去灵岩山寺上香还愿。”
吴行歌感慨道:“原来如今人人艳羡,如今无限风光的梅弗问曾有如此艰辛的过往。”
钱传瓘低叹了一声,“他回梅宅后并未苦尽甘来,仍被二叔所忌,甚至出手暗害。其母以身相护亲尝弗问的每一吃食,某次不幸中了毒虽救回性命却大伤了身子。”
吴行歌感慨道:“听闻梅弗问事母至孝,原是因此。他们母子相依熬过如此多的困苦凶险。他虽身世坎坷,上苍却赐他惊人天赋,十数年间将梅氏发展得如此壮大。”
“世人多知弗问广袖善舞,经商有道,却不晓他另一所长。那却也是我请弗问相护越葳的原因之一。”
望着吴行歌不解的眼神,钱传瓘狭了一下眼道:“他,自其母中毒后便苦研医书,他的医术,不下于寻常太医。”
车外燕啼莺鸣,厢内软毡丝毯,厢内二人目不相交,皆静默无言。梅弗问自斟自饮,仿佛舆厢内仍只是他一人,越葳落落大方的选了个舒服之处倚靠着,心头却难以放松下来。
狭小的空间内有什么正流动着,缓慢而压迫。
她闭上双目假寐,右臂的麻痛比之今晨更盛。清邪丸虽大大压制了‘僵心冻尸粉’的毒性蔓延,右胸处的轻微麻刺感却明白无误地告诉她毒性仍缓慢且不可阻滞地向着心脉侵去。
额头沁出一滴汗珠,又是一滴,渐渐细密,背脊也沾上一层凉湿。她说不清是因为痛,或是这帷幔四垂的厢内的热。
汗越发的细密,而痛感却轻了些。不止是痛感,越葳觉得自己也轻了些,彷佛漂于水中的浮木,又似如丝细雨中风卷起的油纸伞,飘飘无所依,唯向花中去。
花?这花香………脑中闪过一丝清明,这香,非寻常的宁神香,方才上车时还未有异状,他是何时又是如何添加的这味药?
这药是……?熟悉的气味,名字于脑中几乎呼之欲出,却被脑中的那层纱蒙住,纱渐厚渐沉,卷着她不断坠落、坠落……